記憶中的家鄉小菜

每每說及上海菜,最懷念的是愚園路西餐廳的羅宋湯和阿孃家的烤麩。
愚園路上的西餐廳在馬路角過去兩爿店面。招牌和門面裝潢雖考究別致,但並不張揚,有只待熟客之態。服務員穿著絳紅色西裝,帶了白手套上菜。每次去,我媽總是為我倆各自點上沙拉、炸豬排和羅宋湯。沙拉是土豆、豌豆、方腿拌蛋黃醬,而炸豬排則是外脆裡酥,豬肉都能吃出入口即化的奶油口感。而我最喜歡的是羅宋湯。一個小碗伴著銀調羹端上來的一團濃烈紅色,被一層熱油覆蓋。湯底是牛肉和洋蔥,熬透之後加上番茄汁、黃油、捲心菜,還有幾片紅腸。用小勺舀一勺送入口中,那一口炙熱,夾雜著牛肉湯的鮮美、黃油滿口香和一點點辣味,可以在嘴裡回味很久。那湯也不是湯,而是很濃稠的汁,吃的不是湯的後味,而是正正經經每一勺留在嘴裡、包裹整個口腔的醇厚。
小時候的我一面吃一面喜歡往廚房張望,每次總能瞥見一雙手搖一下精緻的手鈴,然後把菜一個個從拱形小窗裡遞出來。我想,手的主人應該是一個又胖又魁梧的俄羅斯人,臉色紅潤,笑聲爽朗。
直到後來出國以後,到處都沒有找到如此熱烈奔放的羅宋湯了。我後來找遍紐約的幾家正宗俄羅斯人開的飯店,找到了原名叫Borscht的羅宋湯,卻都只有味道寡淡的一瓢紅湯,再也吃不到有紅腸的俄羅斯湯。於是,一說是我們當初的羅宋湯是俄羅斯猶太人到了上海之後的改良版,為了符合當地人的口味,加了牛奶和紅腸。一說是十月革命後,俄羅斯御廚都逃到上海租界工作掙錢,而這個黃油濃厚的版本是俄羅斯宮廷版本。兩種說法何者正確,如今已不得而知了。不知道上海的這個門面不大、卻廚藝精湛的西餐廳現在還在不在。
另外一樣讓我念念不忘的是烤麩。逢年過節去阿孃家,一上桌幾盤冷菜,必有烤麩。夾著汁水豐厚的烤麩往嘴裡送,一咬,滿嘴是油;再夾一塊依舊有山土香氣的香菇,滑爽入口,吃得我口舌生香。
阿孃家是寧波人,桌上必定還有嗆蝦嗆蟹和黃泥螺。但當時我尚年幼,吃不慣菜裡撲鼻的烈酒和生鮮的腥氣,從未碰過那些菜。而現在每次去海鮮餐館,總是非要吃生的海鮮,生蠔生蛤生魚等。同行的老外總是奇怪我怎麼不怕腥,我說或許是基因吧,有寧波人基因的我喜歡生海鮮,那股海泥尚未褪去的腥鮮,是我跟故鄉連接最緊密的味道。心事可以藏起來,胃事則藏不住的。
有一次回大陸,我執意要找毛蚶吃。毛蚶是用熱水汆的,然後用個硬幣撬開貝殼,用筷子夾出那鮮嫩的肉,蘸著生薑醋吃。我的執意,便好像要找回童年最清晰的場景。親戚朋友說,那次甲肝爆發之後,上海就不賣毛蚶了。「至今不賣?」我問。「至今不賣,」我叔叔說,「但是我認識個私底下悄悄賣的,可以提前幾天預訂,但是吃起來要偷偷摸摸的。」
後來還是沒有偷偷摸摸地去吃,大家好說歹說,用海瓜子、銀蚶、蟶子餵了我好幾天,我也就假裝忘記了毛蚶的事情。
我外婆那邊也是地道的本地人,上海本幫菜外婆樣樣拿手,即便是家常小菜也是道道入味。一到過年,廚房裡只有兩個灶頭的煤氣爐上,外婆變戲法一樣地可以一下子做上二十多道菜:油爆蝦,白斬雞,響油鱔絲,走油蹄膀,醬鴨,爆魚,肉皮蛋餃湯,八寶飯……一盤盤從廚房裡端上來,冒著熱氣,伴著油香,一大家人便有吃有喝,阿弟姐夫、阿姐弟媳相互隔著巨大的圓檯給對方夾菜,對方便趕緊拿著盤子站起來接,這種不方便承載了熱情和關心。大家吃著,聊著弄堂裡的、外頭的、外國的新鮮事。外公外婆看著滿堂的熱鬧,兩人便滿心歡喜。
外婆的手藝是從她的姆媽那裡學來的,也是她幾十年為一家子操持一日三頓提煉出來的。那些個菜,有些是慢燉微煮,有些是大火熱炒,有些是赤醬濃油,每個都有著地道的本幫菜口味,卻又帶著她的手藝特有的味道。每每吃她做的菜,一股溫潤就從胃裡升起來,像極了春天下午的暖陽。
每個上海姆媽都做得一手直接開飯店的好菜。再擠的廚房,再小的灶頭,都關不住她們魔法般的手藝。包粽子、磨年糕、做豆沙,一雙手能漫不經心地翻著花樣,做出一整套宴席。張家阿婆,亭子間阿嫂,只要鬢角染上一點點白髮,便準是一個私廚高手。
我本以為到了年齡我就會做了,但是,不知是因為這裡的原材料不同,還是我沒得到真傳,至今都未能做出一整桌讓人吃得交口稱讚的菜。
或許是這樣,我就更懷念記憶裡真真切切的羅宋湯和烤麩了。(寄自紐約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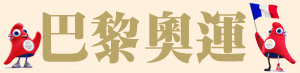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FB留言